《上学前》之《做客》
文/严忠贵
呆在家里久了,闷得慌。有出去做客的机会,比过年还开心,不亚于现在出门旅游。
我妈是婺源游山人,在巍峨的大游山的南面。有时妈带着我们,有时我与二弟孔铭随游山的亲戚去。一般步行去,过了东流大桥,往洞口方向走。经过新村到了江村,有两条路可选择。一条走大路马路,沿山盘旋而上,一会上坡一会儿下坡,九曲十八弯。马路一边是峭壁,一边是被茂盛的灌木掩映的山谷,路上罕见人影,偶尔听到深山中传来野兽的嘶吼。我们总是快步行进,眼睛四处搜寻,心中忐忑不安。偶尔有辆车子、拖拉机之类通过,不嫌其轰鸣吵闹,尘土飞扬也不在意,似乎多了几分安全感。一条是小路,先到洞口村,村口山下有个深不可测的洞,是横向延伸的。后来曾拿着手电筒进去过,脚下是水、乱石,头顶有石缝渗出的水滴落,偶尔有蝙蝠黑色的身影掠过头顶,因为冷不丁,令人毛骨悚然。洞口有凉飕飕、清洌洌的水涌出,在村口几棵老树下形成一个小池塘。从石坝上溢出往南流去,形成一个小小河道,在河道上横跨几根长条形的木板,那便是进村的桥。我们从木桥上经过,如果是早上,可以看到许多妇女洗衣服聊家常的画面。沿一条石板路,穿过洞口村,直到村后山脚下。便沿石板小路拾阶而上,路窄而陡峭,还绕来绕去,藏在枝繁叶茂的树丛中。有的路段,两边的树木枝叶都缠在了一起,像搭起的绿色帐篷。天晴有细碎的阳光泄漏在脸上,雨天有滴答的雨点砸在头上。我们总是紧跟着大人,或簇拥在一起,生怕树林中会窜出什么可怕的怪物。对我们而言,这条小路刺激,有几分冒险的乐趣。大人要我们走马路,而我们常常在小路上攀爬穿梭。
小路下山便与大路汇合,那是一个被周围的山环绕的深谷,马路左侧经常听到机器轰鸣,好像是个采石场,又记得是个石灰厂。再往前走就到了内王塘村,在马路边稀稀拉拉几户人家,稻田却不少,有的季节绿油油一片,有的季节一片金黄,在风中波浪般起伏。与马路并驱而行的是一条小河,清澈见底。热天,我们爬山走路累了出汗了,总会光着脚在小河里玩水,寻找一些凉意。过了内王塘又要爬山了,走马路是一段长长的陡坡,路面凹凸不平,裸露着一些大石头。陡坡尽头是一座山岭,那是大游山向东延伸而来的。这座山岭真像扇天门,南北风光尽收眼底,如果作战,这地利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。站在山岭头,就可以远眺婺源地界游山村的轮廓啦。其实,走起来,还有很长一段下坡路。下坡路在山峦间蜿蜒穿行,渐渐地,脚下一座水库赫然进入视野,被四周的山环抱着,波光潋滟,那是游山人的水库。快到山脚,雄伟的水库堤坝耸立在眼前。下山了,就可以看到田地,看到路边白墙飞檐、雕画古朴的婺源徽式房屋了。
也可以从内王塘村走小路。这一段小路比洞口村那一段就气魄大多了,山高峻,路陡峭,视野更开阔。前面是盆景假山的感觉,这儿才是大手笔,路是大起大落,绵延不绝。山顶有一座亭子,时隔多年,记不清了,似乎亭子砌有白墙,匾额上题有亭名,建在山的最高处,挺大,里面还有两排凳子,是两截长条形的木块。我曾经蹲在那研究过变幻无穷的木纹。站在亭子进口或出口极目远眺,可谓一览众山小。出了亭子便开始走下坡路,总记得秋冬季节,路两边的茅草枯黄了,在风中窸窣作响,萧瑟之中带着浓浓的凄凉。我们曾经看过它们的青葱茂盛,又见证了它们的枯黄衰败。从山上下来,是个幽深的山谷,开始看见梯田、菜地,劳作的游山人。他们的衣着、口音,与我们大不相同,觉得特别新奇。
游山是个大村,有上千户人家,简直像个镇。房屋密密的挤在一起,中间纵横交错着一条条狭窄的石板巷道。村中一条河,不是很宽,东西走向,把村子一分为二,隔一段路跨着一座石桥,或一座木桥,这些桥颇有特色。河两边隔一段距离便两两对称的砌有石板码头,每段码头两头有石板台阶上下。早上,码头上不少是红配绿着装的妇女们在搓衣洗菜,尤其是一些清纯秀气的小姑娘,圆润俊俏的媳妇们,让逛街的男人们流连顾盼,真是风光无限,一饱眼福。河两岸的两条较宽的石板路便成了村子的中心走廊、繁华地带,临河的住户开着小店铺,卖什么的都有,琳琅满目,杀猪的屠户,也把肉案摆在河岸宽阔处。如遇有人家结婚,抑或出殡,那河两岸就热闹了,乐器的吹吹打打、鞭炮的噼里啪啦不绝于耳,那服饰、那仪式别具特色,让我们眼花缭乱。要做具体的描绘,那就颇感遗憾,幼时的记忆已泛黄、斑驳、模糊啦。( 文章阅读网:www.sanwen.net )
大母舅一个人生活,未娶妻成家,以做漆匠为生。似乎手艺不错,画艺书法也颇佳,口碑挺好。油漆的家具古色古香、光滑锃亮,几笔勾勒,题写几个字,颇具艺术性。我们总是到别人家找到干活的他,他个子不高,瘦而精干。看我们去,总是很高兴,热情款待;他的厨艺也不赖。只是住处阴暗,地面潮湿,和我家差不多。另外一家亲戚,妈要我们叫姨妈妈。那是一大家人,我和二弟在那吃饭总觉得拘谨,虽说那小脚的姨妈妈待我们很好,嘘寒问暖、关心备至。看着那年老仍收拾得整齐利索的姨妈妈,总觉得她年轻时一定很漂亮。
还有一条做客的线路,也让我们兄妹其乐陶陶。那就是从东流沿公路往东,经过大路程、余村、到鲤鱼桥,然后从一条便道通往大花桥。我的姑父姑姑住那,他们家也生育了兄妹四人,和我们差不多大。大表妹刘灵莲,文静秀美,二表弟刘文又瘦又高,敦厚友善又活泼好动,三表妹刘水莲那可就调皮了,特爱笑,一有风吹草动,就笑的花枝乱颤。再加上我们兄妹四个,简直成了一个小型旅游团。从我家出发,边走边玩。在大路程的程家堰,看看石碑上的题字,据说是明朝初年留下的。在余村路边,有个土碓,水轮哗哗,水花在阳光下耀眼。鲤鱼桥那座古桥,让我们流连忘返,吸引我们的是关于这座古桥来历的传说故事。桥边还有一棵几个人才能抱得住的老樟树,撑起一片绿色的云雾,据大人讲是有树神的,十分灵异。又听老人讲,解放前鲤鱼桥有国民党的驻军,曾在大樟树下,用酷刑折磨红军战士,然后将他们吊死或枪杀。弄得想象力丰富的我们不敢靠近大樟树,似乎看见了红军战士惨死的情形,或怕树神怪罪。快到大花桥的便道,被两边的山夹住,可谓咽喉之地,地势险要。果然大人说,解放前路北山顶挖有战壕,还有碉堡,仍有遗迹在。路边到两边山下是水汪汪的稻田,绿苗摇曳,或是稻浪起伏。进村是一座古老的石拱桥,石头砌成,半圆的独拱,桥壁上苔痕涂满了绿色,桥檐还有青藤垂挂,乍一看似帘幔。桥下是一条小河,水清浅,卵石调皮的堆叠铺陈在水底,那可是我们的乐园。热天傍晚,我们穿着短裤,光着脚丫,在水里折腾,乐此不疲。
大花桥被山环绕,村外一条河擦身而过,人家不多,和睦融洽,真是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。村子东边那头,是深邃的山谷,田连田似乎连绵无尽头,溪流纵横,一条较宽的土路蜿蜒前伸。我们曾和二表弟刘文去沟溪里抓鱼、翻泥鳅,回来满身满脸泥巴点点,但鱼篓里的泥鳅、黄鳝,拥挤的泡沫腾起多高。姑父个子不高,但能说会道、精明能干。总是热情款待我们兄妹这些小客人,满桌的菜,真不容易,还一个劲地说:吃鸡肉!吃鸡肉!我瞪大了眼睛,找遍了全桌,没看到鸡肉,米粉肉倒是一大钵,心里就奇怪了。回来还和妈说这事,妈听完笑了,说:姑父说的是马佬腔,鸡肉就是猪肉啊。原来如此。
 欣赏佳作!值此中秋佳节来临之际,泪花集真诚祝你阖家幸福!中秋快乐!遥握!2013-09-19 12:49
欣赏佳作!值此中秋佳节来临之际,泪花集真诚祝你阖家幸福!中秋快乐!遥握!2013-09-19 12:49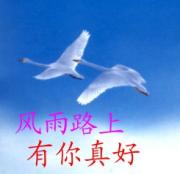 回复@泪花集:朋友,谢谢!顺祝中秋节快乐!2013-09-20 15:41
回复@泪花集:朋友,谢谢!顺祝中秋节快乐!2013-09-20 15:41
